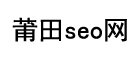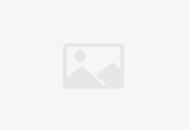色雷斯人
其实,在古代世界各民族或人群彼此交往不多的情况下,对于其它族群的冠名往往会出现此类泛化的现象,亦即将对一个族群局部的认识或称谓,扩大成为更广阔范围内的乃至全局性的族群的称呼。譬如,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就将信奉天主教的西欧人均通称为“法兰克人”;而当时欧洲人也泛称阿拉伯人以及中近东所有穆斯林民族为“萨拉森人”,而萨拉森人起初只不过是西奈半岛上一个阿拉伯部落的名称;欧洲还以“鞑靼”作为中世纪入侵东欧的蒙古人的一种别称,该词实际上也只是渊源于蒙古人中的一个叫作塔塔尔的部落;如此等等。这种古代族名或习惯称谓由泛化而得的现 象,可说是并不鲜见的。起源色雷斯人
色雷斯人的起源不详,究为巴尔干土著,还是来自多瑙河以北的外来移居者,尚无确 凿材料可证,但一般肯定其属印欧语系族群。如果我们确认古印欧人的故土大致可圈定在黑海北岸南俄草原一带的话,那么不妨认为最早的色雷斯先民可能就是从南俄草原辗转迁入巴尔干的游牧部落。有关色雷斯人的文字记载,起初主要出自古希腊人。希腊人从公元前7世纪起开始在色雷斯沿海地区建立殖民地,同色雷斯人渐多接触。活动于前7世纪中叶前后的阿尔基洛科斯,被认为是最早在作品中提到色雷斯人的希腊作家之一。当时他参加了帕罗斯居民赴色雷斯沿海萨索斯岛移民的远征队,在那里同色雷斯人发生过冲突。大概比他更早一些时候的诗人赫西俄德(约前8世纪),也已知道了远在北方的色雷斯,把它看成是刮到希腊的凛冽寒风的策源地。希腊神话中的北风神玻雷阿斯(Boreas),相传即居于色雷斯的萨尔密得索斯,这位诸风之王的形象是满脸胡须,长有翅膀,身强力壮,并穿着引人瞩目的御寒衣服(显然与一般希腊人的装束相异)。荷马史诗曾分别从地名或民族称谓的角度,数度提及色雷斯,而且,《伊利亚特》中提到的色雷斯人,常常是以特洛伊人同盟者的面目而出现的。从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的著述中可见,希腊人对色雷斯人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化了,色雷斯人已成为他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蛮族之一。
分布地区色雷斯人
色雷斯人世代居住的色雷斯地区(Thrace或Thracia/Thrakia),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部,其历史界线曾历经变动。除了庞蓬尼·梅拉以外,古代作家对当时色雷斯的地域范围似乎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大致是以伊斯特河(今多瑙河)之南今保加利亚一带为中心 区域,向南延伸至爱琴海沿岸地区,并包括萨索斯岛、萨摩色雷斯岛乃至累姆诺斯岛,朝北兼及多瑙河以北的达西亚人地区,直抵喀尔巴阡山和蒂萨河上游,东濒攸克辛海(今黑海)、普罗滂提斯海(今马尔马拉海),西邻斯特里蒙河,与马其顿人、伊利里亚人地域相接。色雷斯人
但在更为邈远的历史时期,色雷斯人的居住地域曾比上述范围要宽泛得多,“一度占有过从攸克辛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甚至一直向东延伸到密俄提斯湖(今亚速海)和辛梅里亚海峡(今刻赤海峡)。这就是说,色雷斯人的活动区域不限于古典时代所见的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东北部、土耳其西北端、匈牙利东部一带,甚至还涵盖了今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很大的一部分及乌克兰南部沿海地带。在巴尔干西部,随着伊利里亚人沿亚得里亚海岸的急速南下,色雷斯人为其压力所迫,不得不向东退往巴尔干中部地区。据有人推测,伊利里亚人往东驱逐色雷斯人的时间,约当公元前1300年左右,起码公元前1100年以前,阿克修斯河以西地区已被伊利里亚人所占据。后来马其顿人势力兴起,又进一步将色雷斯人继续向东推压,迄公元前480年之后,斯特里蒙河以西土地便已纳入马其顿版图。这样就大体形成了上述色雷斯地区的西部界线,从而奠定了巴尔干半岛古代族群的基本分布格局:伊利里亚人位居西部,色雷斯人居东部,希腊人居南部,而三者之间的内陆腹地则夹居有混融型的马其顿人。色雷斯人在巴尔干 西部一带的历史性居留,似乎多少仍遗下了一些痕迹,据说其后裔曾一度残留于阿尔巴尼亚沿海的个别岛屿,同伊利里亚人杂居,直至最终被后者同化;色雷斯语言的某些因素也还对日后阿尔巴尼亚语的形成产生过影响。需要一提的是,色雷斯的地理范围有时也被引伸到了小亚细亚的西北部一带,按色诺芬的说法,这里称作“色雷斯的亚洲部分”,其范围从攸克辛海口开始,一直延伸到赫拉克里亚(约当今土耳其埃雷利一带),亦称比提尼亚。在庞蓬尼·梅拉笔下,博斯普鲁斯海峡本身就被称作“色雷斯海峡”。在地名学史上,则素有“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称,正如海峡西端凸吻部的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周边地区古称“色雷斯的三角地带”(Thracian delta)一样。总之,从历史上看,小亚西北部一带可能曾经是来自巴尔干的色雷斯移民的一块留居地,狭窄的博斯普鲁斯与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两海峡从未成为过历史上移民运动的障碍。相传早在大约公元前1200~1000年期间就有色雷斯人跨越海峡进入小亚西北部,后来似乎又一直不断有来自巴尔干方向的移民迁入,在小亚以充任雇佣兵为业。可见,色雷斯的地域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伴随色雷斯人活动的变迁而在空间上有所进退、移易的。
人口色雷斯人
色雷斯人人口众多,依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是除印度人之外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不是因为缺乏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或是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色雷斯人就会无敌于天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而不 至于依旧处在软弱状态。色雷斯族群的人口总数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目,所以当代学者的研究,大体上只能凭藉推测。卡扎劳曾在其撰写的《剑桥古代史》有关章节中,引用了一些有关色雷斯人军队数量的零星材料,再据此而对族群人口数进行估测。色雷斯的奥德里西亚国王西塔尔塞斯(Sitalces)拥有一支大约15万人的军队,其中约1/3是骑兵,其余多为步兵。卡扎劳以奥德里西亚王国约5万平方英里面积可以负担15万人军队的能力推算,认为其全国人口至少已达60万。多瑙河以北盖塔人(葛特人)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作战时,也动用过一支由4000骑兵、1万步兵组成的军队。公元前323年,奥德里西亚王子塞奥底斯三世(Seuthes Ⅲ)能够调集起来对抗马其顿的利西马科斯的兵力,也有2万步兵、8000骑兵。而斯特拉博指出,色雷斯人总体上可为战争提供的军队数量约达1.5万骑兵,20万步兵。今保加利亚学者认为,公元前第1000纪时,仅色雷斯族群中心地带(即多瑙河与爱琴海之间地区)各部落的人口,估计就有百万之众。另据罗马尼亚学者估计,达西亚-盖塔人口可能已达200~250万,或250~300万;而达西亚国王布雷比斯塔(Burebista)即曾拥有一支20万人的军队。考虑到整个色雷斯族群本身十分庞杂,支系繁多,如此看来,其总人口数即使在古代也应该是颇具规模的了,或当在数百万左右。军事色雷斯人的武器品类很多。常见的装备有希腊式反曲剑、匕首、普通短剑、长矛、双面斧、标枪和弓箭。其中,反曲剑的威力极大,让日后的罗马士兵都心有余悸。尽管多数人以轻装步兵形象出现,但部分偏游牧部落也有骑射手部队。在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下,使用反曲弓、钉锤等马战武器。他们还常在其箭镞顶端涂以毒药,用来增加杀敌效果。
护具方面,色雷斯平民一般习惯于赤裸上身,只有贵族们则可以有希腊式铠甲。但是他们却比希腊人有着更厚的亚麻内衬,专门应对寒冷气候。他们还有轻巧的月牙状盾牌,使用木材或柳条编织制成的。外层蒙上皮革,有时在皮革上再饰以铁质或青铜质的环状浮雕,绘制眼睛或者弯月的形状。这也成为外人辨识色雷斯籍士兵的重要符号。
在战术上,色雷斯人习惯于将其军队排成四列。第一列放置较为薄弱的轻装部队,第二列则安排精锐重装士兵,第三列才是预备骑兵。至于全军最末的第四列,主要由鼓动男人勇敢出击的妇女组成。在亚历山大出征色雷斯时,当地人在山间狭道设防,集结了许多车辆组成屏障。最后因无计可施,还将车辆从山坡上推滚下来,企图砸死仰攻的敌人。
色雷斯人
传统的色雷斯轻步兵,是善于袭扰重步兵和骑兵的好手。他们非常能适应复杂地形,经常以不近身的方式作战。除了神出鬼没的透支标枪,也懂得切断水源、夜袭等谋略手段。作为回应,希腊人就发展出了自己的轻装投枪手,用来保护重装部队侧翼。但只要条件允许,希腊军队就会直接从色雷斯部族中征召相关人才。尤其是在不涉及双方的冲突中,色雷斯轻步兵就几乎是希腊重装部队的标配。由于和斯基泰人接触,色雷斯也学会了骑兵楔型阵。贵族往往有自己的重骑兵护卫队,和斯基泰人一样装备鳞甲与护腿。后来色雷斯人还将这种阵型传给了马其顿人,侧成后者的骑兵强国地位崛起。在马其顿王国灭亡的迁徙,又是色雷斯士兵组成了被重建起来的伙伴骑兵队伍。
色雷斯的北方支系达西亚人擅长建筑防御工事,其用材都比较因地制宜。平原地带则就地掘壕,再垒造土墙并树立木栅。在山区则采用石块砌筑堡垒。当今在罗马尼亚境内许多地方,仍可见到从色雷斯-达西亚时代留存下来的工事遗迹。
支系及部落色雷斯人的内部究竟涵括多少个支系或部落,历来众说不一。希罗多德主张为19个,而依照斯特拉博的说法,仅多瑙河以南色雷斯即有22个,嗣后拜占庭的斯特凡努斯则列举出了43个。这个数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有变化的。卡扎劳将其归因于在持续不断的长期相互争斗中,许多较小的部落被最终消灭,或是被较大的部落所吞并。但若全是如此的话,部落数量理应愈趋减少,怎会反倒增多?所 以,也还有可能是由于色雷斯族群内部关系过于复杂,古代不同时期的学者未必都能亲历其境,直接掌握全面情况,特别是那些与周边民族发生过混融的族团,其真实面目往往扑朔迷离,亦此亦彼,莫说古代作家难辨其详,后世学者就更因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而不免掩卷浩叹了。例如,一般已被列为伊利里亚族系的培奥尼亚人(Paeonians),现代学者中即仍有人以其含有色雷斯成份而宁愿将其划入色雷斯族系。据希罗多德所述,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与色雷斯人颇为相似的阿伽杜尔索伊人(Agathyrsi),却被现代学者划入了自南俄草原西迁而来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或萨尔马特人(Sarmathians)族系。此外,作为现代罗马尼亚民族先祖的盖塔人和达西亚人,今多已确认其色雷斯族属,但学术界亦曾长期对此存有过争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此,对色雷斯族群的具体成员及其实际数量要真正达成共识,恐怕并非一桩易事。
色雷斯人
根据我们现今获取的材料,属于色雷斯人族群的大致包括以下支系或部落:居住在赫布鲁斯河(今马里查河)支流阿尔提斯库斯河两岸的奥德里西亚人(Odrysae/Odrysian);居于马其顿东南海岸狭长地带的皮埃里亚人(Pieres/Pierian);居住在奈斯托斯河与斯特里蒙河之间的埃多尼亚人(Edoni/Edones)、萨特莱人(Satrae);栖居在卡尔息狄斯的锡索尼亚半岛的锡索尼亚人(Sithonii/Sithonian),或为埃多尼亚人的一个分支。身份尚存争议的培西人(Bessi),曾被希罗多德称为萨特莱人的支系。还有居于斯特里蒙河以西马其顿地区的比萨尔提亚人(Bisaltae/Bisaltian);位于阿克修斯河右岸的波提亚人(Bottiaei/ Bottiaean)。居于阿克修斯河与斯特里蒙河之间的克列斯通尼亚人(Crestonaei/Crestonii);位于埃诺斯河附近平原的阿普辛提安人(Apsinthii/Apsinthian)。在刻尔松涅斯(今盖利博卢)半岛的多洛科伊人(Dolonkoi/Dolonci);世居罗多彼山东南一带的特劳索伊人(Trausi);位于赫布鲁斯河以西沿海地带的奇科涅斯人(Cicones/Ciconian)。居住在马其顿东部、接近塞尔迈湾一带的米哥多尼亚人(Mygdones);居于罗多彼山和爱琴海之间、阿布德拉城附近的比斯托尼亚人(Bistones);位居潘加欧斯山一带的撒帕伊亚人(Sapaei/Sapaeans)。曾被视为累姆诺斯岛古老居民、后来移居马其顿的辛提亚人(Sinti/Sintian);位于斯特里蒙河西岸、斯科米乌斯山南坡的密底人(Maedi/Maedian)。在赫布鲁斯河与迈拉斯湾之间的科埃拉勒泰人(Coelaletae/Coeletae);在今保加利亚索非亚一带居住的塞尔迪人(Serdi)。色雷斯人
色雷斯人的北支包括盖塔人(Getae,一译葛特人)、达西亚人(Daci/Dacian)。希罗多德曾称誉盖塔人为“一切色雷斯人当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 ,他们栖居于哈伊莫斯山(今巴尔干山)以北、多瑙河下游及黑海沿岸、直至南俄一带。达西亚人住在喀尔巴阡山、特兰西瓦尼亚及巴纳特、克里沙纳、马拉穆列什地区。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常被合称为达西亚-盖塔人;斯特拉博更明确 指出,达西亚人和盖塔人操的是“同样的语言”。托勒密的记载中提到过的达西亚部落据说不下于12个,其中包括:居住在达西亚西部约当今克里沙纳、巴纳特一带的普雷达文西人(Predavensii)、比耶菲人(Biefii)、阿尔伯森西人(Albocensii)、和萨尔登西人(Saldensii);在今达西亚中部地区,从北特兰西瓦尼亚、特尔纳瓦 河地区,向南直达多瑙河畔的奥尔泰尼亚、西瓦拉几亚一带的拉塔森西或拉卡坦西人(Ratacensii/Racatensii)、布里达文西人(Buridavensii)、波图拉坦西人(Potulatensii)及凯亚基西人(Keiagisii);还有居于达西亚东部,即今摩尔多瓦和东瓦拉几亚一带的科斯托博契人(Costoboci)、考科恩西人(Caucoensii)、锡恩西人(Siensii)和皮耶菲吉人(Piefigii)。除了托勒密提及的那些部落以外,达西亚人内部也包含居住在摩尔多瓦的卡尔皮人(Carpi)、居于奥尔特河口的苏契人(Suci)、索梅什河一带的安萨门西人(Ansamensii)以及阿普利人(Apuli)诸部落。甚至达西亚人本身的属名Daci、Dai或许也是起源于他们之中的一个重要部落。盖塔人当中则包括科拉利人(Coralli)、居处多布罗加南部的蒂里齐人(Tirizians)、克罗比齐人(Crobyzi/Crobizians)等部落。曾因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而闻名的特里巴利人(Triballi),亦说可能是盖塔人的一个分支,此外,色雷斯族群还包括生活在多瑙河以南、今塞尔维亚东部及保加利亚一带的默西亚人(Moesi/Moesian),赫布鲁斯河平原产麦区的彼洛格里人(Pyrogeri),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巴斯塔内人(Bastarnae),其下也许还包括皮欧西尼人(Peucini)。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分别 或共同提到过的色雷斯人部落另有帕埃托伊人(Paeti)、德西亚人(Dersaei/Dersaean)、奥多曼蒂人(Odomanti/Odomantes)、迪伊人(Dii)、德罗伊人(Droi)、培尼亚人(Panaean)、第安人(Dian)。色诺芬记载过的一些色雷斯部落名称,则见有米兰狄泰人(Melanditae)、麦林诺法基人(Melinophagi)、特兰尼普赛人(Tranipsae)、蒂尼亚人(Thyni/Thynians)等。其它古代作家提及的色雷斯人部落又有阿斯提人(Astii/Astae)、卡埃尼人(Caeni)、马杜阿特尼人(Maduateni)、科皮莱人(Corpili/Corpilaes)、凯布雷尼人(Cebreni)、斯卡埃博耶人(Scaeboae)、德尔洛尼人(Derroni)、奥雷西伊人(Orrescii)、泰恩特尼人(Tynteni)、布伦纳伊人(Brenae),等等,可能还包括莱吉里人(Ligyri)。
希波战争时期仍留居马其顿北部一带的布利吉人(Brygi/Bryges),亦曾被看成是一个色雷斯部落。希罗多德认为,居住在小亚西北部的弗里吉亚人(Phryges/Phrygians),即源自于欧洲巴尔干邻近马其顿地区的Briges(此或即布利吉人的另一译法)。当他们中的一部分早年移居亚洲时,便改变名称而为弗里吉亚人了。在希腊神话里,弗里吉亚是一个同拥有点金术的弥达斯国王和戈尔迪乌斯之结一类神奇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与国家。斯特拉博也说到过Briges曾有部分渡越海峡进入亚洲而改名为Phryges之事。布利吉人和弗里吉亚人的希腊文表达形式,分别为Βρυγοι/Β1 ριγεζ和Φρυγεζ,从语源上看两者似乎相当接近,或系同名异读。另一位历史学家桑索斯在肯定弗里吉亚人起源于欧洲的时候,曾详细述及其先祖在斯卡曼德留斯的率领下,自攸克辛海西边迁移而来的一幕。可以推知,弗里吉亚人与布利吉人、以至更大的色雷斯族群间可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至于弗里吉亚人由色雷斯地区进入小亚的时间,有谓公元前第2000纪晚期,也有则具体到了大约公元前12世纪左右特洛伊战争时期。以语言背景而论,弗里吉亚语是比较复杂的,常被一些学者视作“与色雷斯语有关系”。
一般认为,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的比提尼亚人(Bithyni/Bithynian)和密细亚人(Mysi/Mysian)大概也是从巴尔干跨越海峡而来的色雷斯移民的后裔,抵达移居地后可能又发生过与本地土著居民的混融。根据阿庇安的记述,比提尼亚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参加特洛伊战争后逃亡的色雷斯人残部,他们大概不是因为找不到船只横渡海峡返回色雷斯而被迫留居小亚,就是回归色雷斯以后因不堪忍受饥馑遂又掉头重返小亚的。希罗多德主张,比提尼亚人的前身是原居斯特里蒙河畔的斯特里蒙人(Strymonii),被逐出色雷斯故土移居小亚之后才改称现名的。色诺芬则直接称之为“比提尼亚色雷斯人”。蒂尼亚人(Thyni)同样也是从色雷斯迁入小亚的。“蒂尼亚人”和“比提尼亚人”以希腊文标示分别为Θυνοι和Βιθυνοι,除前缀外,完全相同。为同名异读,抑或两个单独的族团,尚不能确定,但至少表明他们可能存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小亚西北隅的比提尼亚地名,又有蒂尼亚(Thynia)之称。据说,比提尼亚人的迁移,大约是在早年弗里吉亚人入侵小亚以后接踵而至的。密细亚人的先民也被认为可能源于色雷斯,但古代作家对其文化特征和源流沿革的描述却语焉不详。克罗斯兰认为,密细亚人[最早曾以“穆什基人”(Muski)的名义出现在亚述人的史料文献中]可能比弗里吉亚人更早进入安纳托利亚,后来才作为一种民族的残余形式而见存于密细亚地区。密细亚人大概操一种吕底亚语(Lydian)和弗里吉亚语的混合语言,显然带有民族交融后形成的色彩,不过,这也给其原始身份的辨识造成了相当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欧亚大陆之间这些迁移活动的出现,在时间上似乎都与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约前12世纪左右)相关联,弗里吉亚人、密细亚人与色雷斯人(诸如著名国王瑞索斯带着白色神马助阵的传说)在《荷马史诗》中同被描述为特洛伊人的盟友,这也许不一定纯属巧合。拨开荷马及后人给这场远古战争罩上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薄纱,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那曾是一个爱琴海周边地区形势经历了剧烈动荡的真实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为着夺取各自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希腊人为了突入黑海控制其有利可图的贸易而同扼据海峡通道的特洛伊人进行过十分剧烈的交锋和争斗(大约未必全如史诗所言单纯的美女海伦之争),各种力量出现显著的分化与重组,形成了以希腊各邦为一方、以特洛伊及其小亚、色雷斯各族盟友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间的对峙之势。从当时的利益格局来看,希腊人处在力图改变现状的进攻态势,而特洛伊人及色雷斯诸部则可能极欲维持现状,这也就决定了色雷斯人在战争中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其间风云际会、潮起潮落,或许还曾伴随着频 繁的人群移徙、流动,族邦版图的变迁、进退。恐怕也就在此前后,色雷斯族群本身同样历经着分化流转,引发了其中的几个分支(如弗里吉亚人、比提尼亚人、蒂尼亚人的先民)自巴尔干向小亚细亚的迁徙,甚至不排除也曾出现过某种反方向的移动。这无论从对古代作家留下的片断记载的分析,还是就逻辑推理的一般意义而言,都是不无可能的。
大概正是因为有过如此大范围的迁动,我们才能看到色雷斯族群及其相关支系或裔脉在古典时代巴尔干和小亚西北部呈现的广泛分布的格局。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作进一步延伸的话,就会发现,甚至早自远古时代起即活跃于黑海、亚速海乃至高加索山以北一带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集团,其语言及民族文化背景,据说可能亦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或色雷斯语相关。果若如此,那么,关涉到色雷斯属性的人群及其活动范围也许就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宽泛得多。
对于古代民族状况的描摹和复原,常须借助于对其语言的了解,语言在民族构成的诸要素中,往往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古代语言的内部结构及与其它语种相互关系的性质,甚至可能潜隐着古代人群迁移方向和路线的某些重要信息,所以,语言资料是进行古代民族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指示标尺或参照系。如果我们获取的语言学信息愈是充分,那么,对于特定民族性质的判定及其总体情况的把握就将愈是完整、准确。反之,则会令研究困难重重。
语言古代色雷斯人的语言,是一种直至公元6世纪时尚在使用的活语言,却无相应的文字。一般来说,有关色雷斯人的语言史料是比较稀缺的,用有些学者的话说,“迄今只留下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痕迹”,大体上仅为希腊文手稿中残留的少量简短铭文,其年代可溯自大约公元前5世纪,对这些铭文的解读和词义阐释仍存在不小的歧异之处。其它史料来源还有某些希腊作家著述里发现的边注,包括若干专名语词。而色雷斯语的人名、地名材料则屡有发现,据说,其中仅作为人名的Βιθυζ就有360例,Τηρηζ的132例,Ζευθηζ的115例。
色雷斯语本身十分复杂,与其说是一个方言集团,不如将之视为二或三种紧密相关的语言混融而成的语言,除了严格意义上的“色雷斯语”以外,还有位于多瑙河南北的“达西亚-默西亚语(Daco_Moesian)”。它们在词汇、语词形式及某些辅助语音特点上可能多少存有一点差异,只是这种差别大约尚未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语言。也就是说,依然存在一个颇具包容性的较大的“泛色雷斯语”集团。直至1957年,色雷斯语包含达西亚语在内的这一认识才被正式确定下来,人们亦渐习于广泛采用色雷斯-达西亚语(Thraco_Dacian)这一专门术语。
国家公元前5世纪初,一部分先进部落的社会经济愈益成熟,正在孕育着突破固有的氏族公社制模式。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在波斯帝国征服和占领(前514~前480年)这一外来压力的促动下,南部赫布鲁斯河流域的色雷斯部落逐渐走向统一,这样,“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从而形成了以奥德里西亚部落为核心的国家组织,特雷斯一世(TeresⅠ,约前480~约前450年在位)成为该王国的创建者。其子西塔尔塞斯执政期间(约前450~前424年在位),奥德里西亚王国国力兴盛,广拓疆土,先后降服罗多彼山区诸部落、培奥尼亚人一部,其势力扩至斯特里蒙河与哈伊莫斯山以北的盖塔人地区,还进抵马其顿南部平原和阿克修斯河谷一带。王国的海岸线从爱琴海的阿布德拉,延伸至黑海沿岸的多瑙河口,甚至连黑海西岸的一些希腊人城邦也不得不承认其霸权,并对之缴纳贡金。迄塞奥底斯一世(SeuthesⅠ)治下,奥德里西亚国王乃自称“色雷斯人之王”,其王国每年向内地土著部落和沿海希腊人城市征收的贡赋总额约达400塔兰特4,一度成为亚得里亚海与黑海之间最强大的一个政治实体。人们至今还不太清楚色雷斯人当时如何具体称谓他们的国王,王国究竟是否一直拥有固定的首邑,但可肯定的是,前4世纪时的统治中心是在塞普瑟拉。作为早期国家组织,奥德里西亚王国的统治结构尚颇松散,无常备军,兵力主要靠临时征召。王室的权力通常很大,但国王死后,国土往往由王的诸子加以分割。王室的威权之下,有较低层级的部落权贵,一般直接管辖几块领地,由他们的代表组成议事会,协助国王进行统治。而当王权处于弱势之时,部落权贵往往各自为政,彼此相争。这种局面常为周邻强邦所利用,乘虚而入,酿成分裂。公元前5世纪末阿玛托科斯(Amatokos)为王时,色雷斯人的奥德里西亚王国转而趋衰,前359年终致碎裂为三个不大的部落联盟,其中以塞奥波利斯(在今保加利亚卡赞勒克附近)为首邑的那个联盟存续时间较久。但色雷斯的土地最后仍相继落入马其顿人之手。
卡扎劳提到,奥德里西亚王国衰败之后,在盖塔人中可能还出现过某些王国,大概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在斯基泰人入侵浪潮的面前显得过于突出,首当其冲,结果未能持久。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一个达西亚人王国,亦因被迫对付日耳曼族系巴斯塔奈人的进攻而没有留下多少历史印痕。
古代色雷斯人国家真正取得重要影响的另一例证,便是其北支达西亚人-盖塔人建立的达西亚王国。这个王国的形成,也不外乎内因成熟、外因推动一类的历史条件,由于面临罗马扩张、欲图染指巴尔干的危急之势,而在公元前70年由达西亚人首领布雷比斯塔创立而成。达西亚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特兰西瓦尼亚一带,后期首都即在该地区的萨尔米泽杰图萨。国势全盛时的版图曾西及潘诺尼亚(今匈牙利)平原,东临布格河口,南抵哈伊莫斯山,北达今斯洛伐克山脉。古代铭文曾称誉布雷比斯塔为“所有色雷斯国王当中名列第一的最伟大的国王”,他以大司祭德凯尼乌为自己最重要的首席助手。据信达西亚王国已经拥有法律和法庭、赋税制度。贵族和祭司享有免税、免服兵役的特权。由于战事频仍,它已拥有一支具常备军特征的武装力量。然而,达西亚王国的性质似乎依然显露出某种初级的、原始的痕迹,比较近似于前述奥德里西亚式的欧洲“蛮族”国家,有人称之 为“地域型国家”,谓其本质特征在于行使对辽阔疆域的统治。也有人认为它应属“初期奴隶制国家”,因为奴隶制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仍不大。布雷比斯塔死后,达西亚王国一度中衰,裂解为几个小邦。迄公元85年(或87年)德西巴卢斯(Decebalus)执政后,达西亚王国势力重振,针对罗马帝国的强权压境,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抗击。虽在89年挫败了皇帝图密善的入侵,但最终在101~102年和105~106年的两次达西亚战争中为皇帝图拉真所败,达西亚王国遂告灭亡。毕竟,这也称得上是古代色雷斯族群社会历史演变进程中富有特殊意义的煌煌篇章。
城市典型的色雷斯语地名成份有:_dava(“城镇”)、_bria(“城镇”)、_para(“村落、定居地”)、_diza(“设防城镇”)、_sara(“河流”)、_upa(“水”)等。由于语言背景仍存差异,这些地名的分布在不同地域则是不均衡的。例如,带有_dava后缀的Acidava、Burridava、Sacidaba等,基本上是达西亚所特有的,在默西亚和色雷斯地区则难于见到。在多瑙河以南地区,_bria被用于象Μεσημβρια、Πολυμβρια、Σηλυμβρια一类复合词。而带有_para后缀的地能见到潘加欧斯山一带由奥多曼蒂人、皮埃里亚人和萨特莱人诸部落开发经营的金银矿。在诸如赫布鲁斯河一类河流中,也一直在采用原始的淘金法由泥沙中采掘零散的沙金。虽则古代文献的某些统计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从不少色雷斯部落大量存在银质铸币这一事实来看,当地矿山开采业的活跃、金属加工技术的娴熟,恐怕已是毋庸置疑的了。而地处北边的特兰西瓦尼亚一带,达西亚人也在开发金矿,由其制作大量钱币、饰物而可推知,大概也已采掘银矿资源了。由于内陆地区多不产盐,色雷斯人为了获取对盐的基本需求,不得不倚靠向沿海的希腊人购买,以出售本族奴隶来换取盐。贸易活动的范围,还涉及向希腊人地区输出木材、粮食、酒类、矿产品,这就构成了古代色雷斯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色雷斯不同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大都在年度定期集市上进行。在色雷斯,与繁荣的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城市生活,至少在罗马时代以前还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不过,自公元前7世纪以降,希腊移民则已开始在爱琴海与黑海的色雷斯沿岸一带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城市,譬如,今希腊境内的阿布德拉(奈斯托斯河口附近)、今罗马尼亚境内的伊斯特洛斯(罗马人称希斯特里亚,濒临锡诺耶湾)、卡拉提斯(今曼加利亚)、托米(今康斯坦察)、位于今保加利亚境内的奥德索斯(今瓦尔纳)、阿波罗尼亚(今索佐波尔)、麦森布里亚(今内塞伯尔)、昂恰卢斯(今波莫里埃)、在今土耳其境内的埃内兹(赫布鲁斯河口)及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等。这些希腊人的沿海城市与近旁的色雷斯部落相毗邻,不但成为了这一带的经济贸易中心,同时也对当地居民起着一种文化示范的作用。色雷斯人同希腊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常常就是经由这些殖民城市而展开的。尽管色雷斯人大部分依然散居于各处山地、平原乡村,落后的多布罗加地区居民中甚至还有不少“穴居人”存在,但至古典时代,他们亦开始兴建起一些设防的城镇。由保加利亚考古学家发掘的原修梭波利斯城遗址,城墙已厚达2米,墙上并筑有防守的角楼。其它知名的色雷斯城镇还有:塞普瑟拉、多里斯库斯、克桑瑟亚(今希腊克桑西)、彼齐耶等。此外,在今罗马尼亚境内则发掘了一些达西亚人的城镇或要塞,象科斯特什蒂、格拉迪什泰、蒙塞鲁卢伊等。它们往往建在便于防卫的小山顶上,得以俯临、控扼通衢大道;并砌有高大的围墙,木石结构的墙基,泥砖作墙体,隔一段距离就矗立起一座方形塔楼,最高一层平台上所立的塔楼,多系酋长的居所。这种设防定居地的出现,一般预示着色雷斯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正开始趋于稳定化。
社会发展水平色雷斯人各部落的社会发展水平各自呈现不平衡状态,但其内部发生不同程度的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色雷斯人流行文身刺青的风习,希罗多德指出,刺青被认为是高贵的标志,身上无刺青者则被目为下贱之人。凡无所事事或靠打仗、劫掠为生的人,被认为是最具尊荣地位的,而以农耕为业的劳动者,则受到蔑视。显然,这同塔西佗笔下日耳曼人军事民主制的社会风貌颇相类似。色雷斯人的某些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贵族和平民阶级,色雷斯语里称贵族为zibythides。达西亚人的贵族即有tarabostesei(戴帽者)之谓,亦称pilleati,因为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头戴这种显示特殊身份的皮帽(pilleati),而普通平民一般却无权戴帽,遂称comati或capillati,意即“蓄长发者”。贵族可出任国王、祭司,大多充任武士,平民则只能从事低贱的农耕劳作。在一些色雷斯部落(例如凯布雷尼人、斯卡埃博耶人)中,国王的身份和祭司的权力有时是二者合一的,最高统治者亦即祭司本人;而另一些部落(象达西亚人)的国王权力却又是与祭司区分开来的。
奴隶制在色雷斯人里奴隶制可能已然流行,希罗多德说他们有时将儿童出卖为奴。掳获战俘、诱拐和奴隶贸易的活跃,使得大批色雷斯人流入希腊及后来的罗马奴隶市场。在雅典戏剧人物中,Davus、Geta一类往往是色雷斯男奴、女奴习用的名字。罗马人致力于从骁勇的色雷斯奴隶当中选拔角斗士,著名的罗马奴隶大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可能来自色雷斯的密底人部落。显然,这些色雷斯奴隶是作为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的一部分、以其附属品的面目而出现的,但色雷斯人各部本身奴隶制的发展却不十分清楚,大概也程度不一。据罗马尼亚学者的看法,在其北支的达西亚人-盖塔人之中,大概只存在一种宗法制类型的奴隶,经济上不占重要地位,仅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进入市场。
色雷斯人
尽管古代色雷斯人社会经济的总体状况仍然不高,大都处在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然而同上述发展不平衡的事实相适应,在他们的一部分成员当中其实已经开始萌发了早期的国家组织类型。
信仰古代色雷斯人极富特色的精神生活,是与他们社会经济生活的特定性质及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色雷斯人的宗教属多神教,以各种自然力为崇拜对象,并赋之以人的形貌性格,体现了古代宗教中常见的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
色雷斯人似乎也象其他印欧语系民族一样,崇奉共同的天空之神帝奥斯(Dios),那些带有dio、deo或deos字头的人名和部落名称可资佐证。他们尊奉的次一等的神祇有兹贝耳苏尔德(Sbelsurdos或Zibelsurdos),大概是雷电之神。有的色雷斯部落还祀奉一位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Hera)那样的女神,色雷斯内地发现的许多罗马时代祭坛的雕像,即为赫拉。其实色雷斯人崇拜女神的传统由来已久,P.德特夫早先曾提及发掘到的许多孕妇的塑像,据认为,可能这同地中海地区古远的对“伟大母亲”(或称大母神)的崇拜(母性崇拜)风习有关。
色雷斯人也祭奉近似于希腊神祇赫利俄斯(Helios)一类的太阳神,相传赫利俄斯每日清晨驾驭着由四匹喷火神马曳引的太阳车,从东方冉冉升现,巡游苍穹,及至傍晚时分才消失于西方的大洋河里。这位神祇是同马匹、车辆联系在一起的,凸现了自很早时候起即使用马车的印欧民族的文化表征。希腊戏剧大师索福克利斯就曾将赫利俄斯称作为“爱马的色雷斯人的主神”。与色雷斯人同源的比提尼亚人,曾习惯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举行法庭审判,他们面朝太阳,以便神能从旁直接观察其审判的过程,于是太阳神便又具备了主持公正的审判之神的身份和功能。色雷斯人对赫利俄斯的祭拜后被俄耳甫斯教(Orphism,一译奥菲士教)所吸纳,在此赫利俄斯已被视同于狄奥尼索斯(Dionysus)了。俄耳甫斯教与色雷斯传统是有关联的,传说该教由色雷斯王与缪斯女神之子、英雄和游吟诗人俄耳甫斯创立,为一种出现于公元前8~6世纪的秘传宗教。相传俄耳甫斯最终在一次祭奉酒神的仪式上遇害,尸体被撕裂成碎片。俄耳甫斯教十分强调躯体死亡后的因果报应和灵魂转生。在其神秘祭礼中,往往以动物代表神的形象,信徒撕裂动物而活剥吞食,谕示着将神体摄入自身,从而获取神性。但另一方面,俄耳甫斯教又力主节制饮酒、肉食及性行为,亦即通过某种程度的禁欲而对粗野的酒神崇拜作以一定的改良。
酒神崇拜的主要对象是狄奥尼索斯,亦即罗马人的巴克科斯(Bacchus)。狄奥尼索斯是古代希腊诸神中最负盛名的神祇之一,他的形象不是被塑造成一个俊俏的美少年,就是一个抱在畜牧、商旅之神赫尔梅斯(Hermes)手中的男婴。然而,他又常被人与萨巴齐奥斯(Sabazios)相混同。其实追本溯源,狄奥尼索斯和萨巴齐奥斯都是最初出自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的神祇,同属色雷斯人的名字。对狄奥尼索斯的祭拜起初大概仅在哈伊莫斯山、罗多彼山和皮林山地区,后渐扩展。以往认为,公元前第1000纪初期,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即已传入希腊5,其具体传播路径大概是经由小亚 细亚的希腊人居住地区而来的。后来的研究表明,希腊人接受狄奥尼索斯崇拜的时间可能还要比之早得多6。希腊人似乎先是经过激烈的反对,尔后才接受对他的崇拜,据说雅典更是在得悉德尔斐的神谕之后始将其祭仪列入城邦正统仪式的7。狄奥尼索斯神象许多古代神祇一样,具有多重的属性,他起初是植物神、丰产神,尔后更以葡萄种植和酿酒业的保护神而闻名。相传狄奥尼索斯为宙斯之子,曾被交由倪萨山的神女们抚养。他的显现形式之一是常春藤,色雷斯人常用它来缠绕在武器上。有时狄奥尼索斯又被赋予了动物、尤其是公牛的形象,相传他是在变作公牛外形、以躲避提坦诸神的攻杀时遇害的,被剁成了碎块。狄奥尼索斯祭拜是一种以男性生殖器崇拜为主要内容、祈求丰产的祭典。祭仪举行之时,参加者(多系妇女)往往头戴常春藤冠或面具,有的还戴上牛角,模仿其形象,手执酒神杖及阳物模型,身披兽皮,载歌载舞,用笛子吹奏出刺耳的乐声,一路游行一路呼唤着神的名字,喧嚣恣纵,状若癫狂,也有随后撕裂并吞食用作祭物的活牛。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这番祭礼之后,方可获得神力,感到自己与神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狂野的祭礼甚至也同古老的人祭风俗相涉。据希腊传说,底比斯王彭修斯和色雷斯的埃多尼亚王莱克尔加斯因反对狄奥尼索斯祭礼,最终竟被其疯狂的信徒所杀,尸体撕裂成碎块,按习俗撒入地里肥田,大约是意在求得狄奥尼索斯神降赐丰收。远古时期的部落酋长或国王似乎经常扮演这种奇特的神的角色,后又往往以神的身份、神的象征而被处死肢解,重又回祭给神祇,这在许多民族的古老神话中都是不乏其例的。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在东地中海地区曾经颇为流行,其遗迹在色雷斯、希腊和小亚细亚各地均不难寻觅。能得以如此广泛的流布,恐怕也是由于这种古代宗教本身“对于热爱神秘并自然地倾向于复返原始状态的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的缘故,此外,或许还在于它流露出的某种不拘陈规、敢于同专制而正统的希腊奥林波斯山神系相抗衡的鲜明色彩。
与狄奥尼索斯一起从色雷斯传入希腊的,还有她的母亲、女神塞墨勒(Seleme),或即色雷斯-弗里吉亚人古老的大地女神(Earth_goddess)。塞墨勒与宙斯的结合,诞生了狄奥尼索斯,这大约不过是印欧诸族神话里屡见不鲜的天神与地母婚配这一模式流行于色雷斯人中的一个翻版而已。
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狩猎和生育之神阿耳忒弥斯(Artemis),也是一位被看作来自色雷斯的重要女神。希罗多德早已提到了她同色雷斯人之间的关系,并言及色雷斯人和培奥尼亚人妇女习于向她呈奉用麦草包起来的贡品。由此可见,阿耳忒弥斯也具有明显的丰产女神的寓意。同时,她又是一位狩猎女神和动物的保护者,典型的阿耳忒弥斯显现为一袭猎装、背负箭筒的少女形象,身旁伴有一头赤牝鹿。很自然地,她被视作“一位丰产保护神”,一位与母性及所有其它同佑护生命、促进土地丰产一类的行为相关的神祇。阿耳忒弥斯最初在色雷斯时是否有过其他色雷斯名字?不见载录。以希罗多德的广博见识和有闻必录的行文风格,在他的著述中是应该会提及的。但阿耳忒弥斯又确曾在很多地方受人膜拜,有过各种别名,譬如俄耳提吉亚(Ortygia)、库忒蕾亚(Cytherea)、铿提亚(Cynthia)等,这大约意味着她的形象原本或许就是一个糅合了不少地方性神祇在内的综合体。似乎从很早时候起,阿耳忒弥斯即同色雷斯人的战争和狩猎女神、或是弗里吉亚人的月神本狄斯(Bendis,亦称本狄达Bendida)混为一体了,与之相混的还有古老的司魔法和魅力女神赫卡忒(Hecate)。赫卡忒的灵兽是狗,在萨摩色雷斯岛6泽林西亚的山洞和与该岛相对的色雷斯沿海一带,此岛名称Samothrace,意即“色雷斯人的高岛”,因岛上有爱琴海一带最高峻的山峰,沿岸自古即为色雷斯人居住之地(参阅邵献图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第373页“萨莫色雷斯”条)。
就流行着以狗作牺牲向她献祭的风俗。对本狄斯的祭奉习俗,至少在伯里克利时代已经被引入希腊雅典,柏拉图曾提到过比雷埃夫斯港本狄斯神庙的首次节庆(据说当于公元前429年萨尔盖里月19日),从中可见由雅典公民、特别是定居在比雷埃夫斯的色雷斯人参加的献祭、赛会和火炬赛马等活动。在希腊的浅浮雕作品里,本狄斯被描绘作一身色雷斯人装束。据说她也曾受到北方达西亚人的祭拜。本狄斯具有的某些特性,事实上还会使人将她同希腊家灶女神赫斯蒂娅(Hestia)联系起来。与本狄斯或阿耳忒弥斯关系密切的另一位色雷斯女神是科提斯(Cotys,或科提托Cotytto),她也是色雷斯埃多尼亚人的女神。对科提斯的祭拜,大概是沿着贸易商路一线而辗转传入希腊的,在雅典、科林斯均曾流行过这种秘密祭礼。当秘祭举行时,往往伴以狂舞淫乐,男人身被女装登场,极富恣肆放荡的色彩,其狂欢气氛足可与祭祀狄奥尼索斯的酒神节庆典相比拟。
依照斯特拉博的记述,对科提斯的狂欢秘祭与在雅典的对弗里吉亚人大母神赛比利(Cybele,一译库柏勒)的祭仪相似,亦即具有祭奉众神之母、丰产女神的性质。其实,弗里吉亚的赛比利崇拜在上古地中海世界诸民族的生活中曾经盛极一时,从很早时期起,便同希腊人对母神瑞亚(Rhea)、罗马人对播种和丰饶女神俄普斯(Ops)的崇拜混合在了一起。这种赛比利崇拜很有可能同前已述及的色雷斯人中间广为流行的“母性崇拜”古老风习存在着文化上一定的关联。
色雷斯人自古擅长音乐、舞蹈和诗歌,希腊文化深受其濡染。在希腊神话里,缪斯(Muses)是一群司艺术、诗歌与科学的女神,形貌姣好,多才多艺。据认为,希腊对缪斯女神的崇拜肇始于奥林波斯山麓皮埃里亚一带,在此建有最早的祭奉神庙,其早期信徒源于一些色雷斯人歌手。
不同民族古代宗教中神祇形象与功能的混融及彼此借鉴,揭示了他们之间曾经拥有过相近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至少体现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关系。带有色雷斯色彩的除了那些名号各异的女神外,也还有别的一些男性神祇值得关注。希腊神话中的战神阿瑞斯(Ares),常与罗马战神玛尔斯(Mars)相对应,在古代艺术家的雕塑作品里多以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的形象出现。他也被认为是可能源自色雷斯的,有的学者干脆直呼其为“色雷斯所奉之神”。在埃多尼亚人和比萨尔提亚人的部落系谱中,阿瑞斯即扮演着某种角色。不清楚的是,色雷斯人本身供奉的战神真实名字究竟为何?有人猜测,希罗多德提到的阿普辛提安人的普雷斯托洛斯神(Pleistoros),或许就是该部落的一位战神。而克列斯通尼亚人的战神,则名为坎达翁(Kandaon)。阿瑞斯之引进希腊,大概是没有太多疑问的,一般认为,他至少在荷马时代已经传入,跻身于奥林波斯山诸神之列了。需要一提的是,阿瑞斯在希腊不太受欢迎,对他的崇拜也不流行。其原因看来不光在于战神原本即为凶残暴戾的化身、令人生厌这一点上,恐怕更是由于荷马史诗述及的阿瑞斯帮助特洛伊人参战,曾与希腊人为敌。不过,如前所述,这倒恰恰体现了特洛伊战争中色雷斯人诸部通行的政策取向,印证了残留在阿瑞斯神像侧背的色雷斯遗痕。
在色雷斯人倾注了浓重宗教情感的诸神当中,盖塔人的冥神扎尔莫克西斯(Zalmoxis)是颇富特色的。后人对其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希罗多德的生动描述。盖塔人自认为是长生不死的,凡死者都不过是到扎尔莫克西斯神那里去了。每隔四年,他们就会以抽签的方式挑选一个人作为信使,派去面见扎尔莫克西斯,以便通过他向神陈述他们的需求。派遣的具体作法是,将这位使者抬起抛向空中,而让另一些手执尖矛的人在下面接住。若使者落下时被竖立的矛尖戳死,则意味着他被神所接受;若侥幸未死,却被看作是一个神不予接纳的坏人,须另换一人去代替他。显然,这种血淋淋的向神派遣使者的风习,实质上不外是一种以活人献祭的古老习俗的残留。起初,这种人祭仪式大概是每年举行的,后来则间隔期渐趋延长。古代社会曾流行定期杀死所谓植物精灵、以求得土地丰产的原始之俗,从这个意义上,扎尔莫克西斯似乎可被视作盖塔人的植物神。而另一方面,扎尔莫克西斯也自然地充任了司掌阴间事务的冥神角色,尤其还被看成是向人发布预言和启示的神或蓝色明朗的天空之神(a sky_god),这位天空之神的别名或许又叫盖培列齐斯(Gebele?zis)。关于这位扎尔莫克西斯的身世,曾颇多传闻。据说他因一出生即披着熊皮(Ζαλμοζ),而由此得名。希罗多德还提到,扎尔莫克西斯原是一名希腊人的奴隶,后获释并得到财富与知识,返回色雷斯始行传教,应允给予人们永生和幸福,深受色雷斯人的尊崇。对扎尔莫克西斯神的崇奉,不仅在色雷斯人里有影响,而且据说还残留至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的传统之中。
如果说,在色雷斯诸部的原始信仰中尚难以找到比较成熟的宗教组织的话,那么盖塔人的扎尔莫克西斯崇拜倒似乎已然形成了某种系统性的东西。达西亚-盖塔人里有极具地位的祭司阶层,他们既是占卜者,又是医生,照例要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食用特定的食品,祭司们还给自己制定了一套谨奉遵行的禁欲式则律。在普通祭司之上,又以大祭司为首,他对于人们来说几同于神,因而须得服从其旨意。大祭司通常住在高峻的科盖奥农山(约当今罗马尼亚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奥尔泰尼亚交界处一带的古古山)的一个岩洞里,而高山之巅一般被认为可能是最接近于上天的地方。祭仪通常包括祝祷、礼仪、诵念符咒。举行祭祀扎尔莫克西斯神的仪式往往就选择这样的高山绝顶,在一矩形或圆形的祭坛内进行。在今萨尔米泽杰图萨发现的矩形祭坛,由一连串石柱或圆木柱构成;圆形祭坛则由排列成环形的石柱构成,此外,还见有一种象征太阳的安山岩祭坛,即以一块圆形石板为中心,四周排列着十块象征光芒的石板。在原始宗教中,其组织及仪规都有些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德教相类,亦显得颇具程式化了。
此外,色雷斯诸神中还有一位地位显要的成员,希腊化时期的色雷斯人称之为“赫洛斯”(Heros),可能就是后人从罗马帝国遗物里获知的那位色雷斯的“骑马者”(Horseman),其石雕像和青铜塑像仅在保加利亚境内就多有发现。他具有冥间之神的性质,另外也是植物神以及所有自然产品的赐赠者,以致于在约公元前2世纪的奥德索斯城钱币上便将他刻画成了有着象征丰饶的羊角状饰物的形象。此神出现在碑铭中的色雷斯语名字大概是德尔泽拉斯(Derzelas)。在托米、伊斯特洛斯、卡拉提斯等黑海沿岸希腊人城邦里,这位色雷斯神一般被视同为希腊人的冥神,他也被当作是赋予人们健康、保证其房舍和行旅安全、以免遭灾祸的保护神,还常常以狩猎之神的身份而出现。据推测,色雷斯人中可能也曾有过类似于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医神,与希腊山林水泽仙女相对应的泉水女神,等等。由于时光流转,过于久远,色雷斯人的固有宗教在历史的溪流中渐至湮没无闻,其神祇意象模糊,不少要素竟最终被希腊人的宗教所容纳。因此,探究色雷斯人的精神生活,是离不开对古希腊宗教的深入挖掘的。
至于色雷斯人与神交往的方式,实际上也还带有十分显明的原始色彩。据希罗多德介绍,盖塔人有一种奇特的风习,雷暴雨时他们会对着空中射箭,以威吓带来雷鸣电闪的那个敌对之神。他们企盼蓝色明朗的晴空,不愿面对雷电交加这一可怖情景而又试图予以制止,于是只得将它归咎于不可捉摸的神在作祟,从中折射出的正是其畏惧自然却又不肯甘心就范的心态。以威吓或警告的方式表达意愿,是否意味着他们与神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通过祭奉而达到彼此沟通的交往上的障碍呢?当原始人的意识里充斥了无所不在的“邪魔”而倍感困扰的时候,诚如弗雷泽所归纳的,他们往往 会采取种种不可思议乃至荒谬绝伦的“强力的驱邪形式”,他们此刻或许并不在意其真实的效用,而更注重于形式的本身。
这种思维和行为上的原始性,从色雷斯人依旧保持人祭习俗的记录里也不难窥得。希罗多德已经描述过盖塔人祭奉扎尔莫克西斯神时那种使人毛骨悚然的祭仪,另外,他还列举了希波战争期间阿普辛提安人将波斯战俘当作牺牲向他们的神献祭之事。其实在世界诸民族童年时期的宗教生活中,几乎都曾经历过这个盛行人祭的阶段,用伏尔泰的话说,那时人祭“几乎血染整个地球”。
与人祭现象同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还有嗜血的人殉习俗。据希罗多德记载,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色雷斯人中,尚残留着将已死男子的某个宠妻杀死在墓旁以作殉葬的风气,甚至还会因此而在死者众多的妻子之间引起谁是最得宠于丈夫的争论,其他未被入选陪葬的妻子竟会以此为耻。这种近乎不可理喻的漠视生命的态度,可以说,是同当时流行灵魂不灭、主张人能长生不死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出于同样的信念,特劳索伊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也是颇堪玩味的。当孩子出生时,亲戚们却围坐在一起悲叹不已,历数着孩子未来一生将要遭遇的种种灾祸;而当他们为死者送葬之时,却反而表现得轻松欣喜,因为在他们看来,死者总算从生活中所有的不幸里解脱出来,达到了完满幸福的境地。死亡对于他们,并非生命的终结,不过是人生途程中走向一个新阶段的转换而已。
希罗多德记述过色雷斯人上层社会的葬俗,反映的恐怕也还是类似的观念。一般是将死者遗体陈放在外供人哀悼三日,继则献以动物牺牲,再举行饮宴。遗体或付之火葬,或不加火化而直接葬入地下,筑起墓丘后,还举行一种类似丧葬游戏的竞赛,竞赛最难者则被授以最高的奖赏。上个世纪在保加利亚各处所作的考古发掘已证实,色雷斯人的墓葬中确有相当部分属火葬性质,其余的则为土葬,不少墓内都发现有随葬品,不但包括一般的生活器皿、武器之类,还有以死者生前马匹随葬的,倒是颇与其南俄草原邻居斯基泰人的葬俗相近。
作为巴尔干地区一支古老的印欧语系族群,色雷斯人具有自己极富特色的民族性格、语言、习俗和历史传统,形成了大体统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尽管就总体发展水平而言,古色雷斯人尚未脱古朴稚拙的原始文明范畴,无难同希腊罗马比肩,但在地中海世界诸种文明林立、互见融汇与竞争的环境里,仍有其独具魅力的一席之地,也给周邻民族尤其是希腊人的文化以富有价值的影响。
尾声从上古时期起,迄于中古,色雷斯族群在与不同外部势力的交往和冲突中,逐渐发生了分化、裂变。居住在今保加利亚境内的色雷斯人先是沦入马其顿-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前2世纪后该地区又为罗马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熏染下,直至拜占庭时期。公元7世纪末,由于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的相继入侵,本地的色雷斯人遂被同化,共同熔铸为后来斯拉夫化的保加利亚人。早年残留在巴尔干西部的少量色雷斯人,则在大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就同占优势的伊利里亚人渐相混化,至中古时孕育出了阿尔巴尼亚民族。而色雷斯人北方支系的达西亚人-盖塔人,自公元2世纪初其王国灭亡时起,即被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后与入居当地的罗马移民发生融合,实现了罗马-拉丁化,由此形成罗马-达西亚人,亦即后来罗马尼亚人的先民。一般认为,近现代民族往往是在古代民族分衍、重组与再融聚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色雷斯人的成员主要参与了近现代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过程,也部分地对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乃至希腊、土耳其民族的形成施加了影响。如果说,当今的巴尔干诸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分别由不同成份、不同色调的古代民族因子依循不同的比例调和、混融起来的,那么,色雷斯人大概就构成了积淀在这块巴尔干民族文化调色盘中的为数不多的几片底色之一了。研究巴尔干和欧洲的民族历史,恐怕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