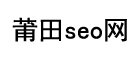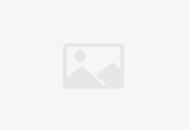“索隐派”红学的开山鼻祖、著名学者周春。
周春(1729—1815),字松霭,号屯兮,晚号黍谷居士,海宁人,著名学者、藏书家。乾隆十九年进士,曾任岑溪知县。他博学多识,一生著作颇丰。他的出生时间仅比曹雪芹晚十四年,可算是曹雪芹的同时代人。他研读《红楼梦》的成就体现为所著的《阅红楼梦随笔》,书中有本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的自序,可以证实是目前所知《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
周春在本书中主张《红楼梦》“写张侯家事”,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的鼻祖,结果被周汝昌先生讥讽为“红学在东南半壁一兴起,那兆头就不怎么美妙”。
周春文中记载“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证明了早在程高整理出版《红楼梦》之前就有一百二十回本的存在,推翻了胡适先生考证的高鹗续写《红楼梦》的结论。
周春于乾隆五十九年撰就《阅红楼梦随笔》。全书计有《红楼梦记》﹑《红楼梦评例》﹑《红楼梦约评》,内容驳杂,分条评述,或三言两语或二三百字。其中有的评论不乏见地,如他说:“阅《红楼梦》者既要通今,又要博古,既贵心细,尤贵眼明,当以何义门评十七史法评之。若但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法评之,浅矣。”还说:“天下阅《红楼梦》者,俗人与《金瓶梅》一例,仍为导淫之书,能论其文笔之若何,已属难得……”说读《红楼梦》要博古通今,心细眼明,不能把《红楼梦》视为淫书,不能只以金圣叹评“四大奇书”的评法评《红楼梦》,这些都是正确的见解。他认为《红楼梦》是叙写“金陵张侯家事”,证据是“张氏与曹氏有通家之好,雪芹时常过从,目击其家庭一切,涉笔成此杰作”。但他的“张侯家事说”破绽太多,且不能自圆其说,后世赞同这种说法的寥寥无几,影响不大。作为早期的红学家,就其思想方法和学识见解而言,是缺乏科学性、准确性的。
但是他的这种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历史人物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的考证方法,可以说是开了《红楼梦》索隐的先河。从清末到“五四”,在“红学”研究上,索隐派红学家著书立说,众说不一,但所用的方法同周春毫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他举为“索隐派红学”的开山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产生《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话,一般的读者是不大注意的,而直接从“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读起。研究《红楼梦》的人可是不同,他们难得在作品中发现作者的自白,因而如获至宝,格外重视,很想通过解读这段话,找到最终找开《红楼梦》之谜的钥匙。
特别是这段叙述中渗透出一种真真假假、若隐若显、扑朔迷离的气氛,增加了人们解读的兴趣。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将真事隐去那么到底隐去的是什么事呢?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而书一些带忏悔意味的话,似乎是在回忆一个人家族中的往事,所以便有人猜测:《红楼梦》可能写的是清初某一个家庭。
而一般家庭又不会有“天恩”,于是又进一步猜想,可能是康熙未年“一勋贵家事”。这样看来,索隐派的产生倒也顺理成章。作者自己一定要那样说——隐去了真事,还能怪读者沿着作者所说的方向去七想八想吗?
这种关于《红楼梦》写的是哪一家的家事的猜测,开始比较分散,有的说明珠家,有的说傅恒家,有的说张侯家。辗转相传而为更多接受的是明珠家事说。一则因为《红楼梦》里贾府的遭遇与大学士明珠一家的荣枯不无相似之处,都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二则是纳兰公子的性格才情,使人联想到贾宝玉的性格。
明珠家事说的广为流传,还和乾隆对《红楼梦》的看法有一定关系。只是比较起来,早期索隐派中还是以明珠家事说的影响最大。早期索隐派的特点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
索隐派红学的大规模兴起是在清末民初,当时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历史时刻。觉醒了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惊异地发现,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恰恰是小说这种形式。三十年代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陷中国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们的种族思想再次被唤醒,以弘扬种族思想为特征的红学索隐又跃跃欲试,正不足怪。[1]
发展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挥的对索隐派红学的打击力量,主要在于他发现了大量的有关《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和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早期抄本,证明《红楼梦》是以作者身世经历为底本的文学作品,不是明清的宫闱史的变换,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生活的翻版。
在胡适提供的大量证据面前,索隐派红学一时间陷入了困境。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虽然回答了胡适对索隐派的批评,但申明的理由仍嫌薄弱得很,不足以重新巩固己说。无论如何,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后,索隐派红学从发展趋势上已进入衰竭时期。
但发展趋势上的衰竭不等于索隐的方法没有再用,即使考证派红学成为主流的学派,踞于“艳冠群芳”的地位,仍不断有索隐派的文章与著作公诸于世。其时,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品: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辩论》、景梅九:《红楼梦真谛》。
复活索隐派红学在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的打击之下,自二十年代以来便进入了衰竭时期。寿鹏飞、景梅九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影响并不大。四十年代方豪发表《红楼梦新考》,表示确信顺治与董鄂妃恋爱故事说“有一部分是真实性”,只是一笔带过,未做任何论证。
五十年代以后,索隐派在大陆基本上消失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隐派在大陆上虽基本消失,却在海外得到复活。其间代表作品有:杜世杰:《红楼梦原理》、李知其:《红楼梦谜》、赵同:《红楼猜梦》。
传承索隐派红学的产生,除了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明初民主革命的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的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仍不时地为人们运用。[2]
从胡适先生1921年推出“曹雪芹自传说”以来,经其几代弟子的承继和推广,已经占据了红学研究的主流,考证曹雪芹家族的史料,并套在《红楼梦》中人物的身上,成了红学研究(实质上只是曹学)的主要工作,自号“考证派、新红学”。
在考证派“新红学”一枝独大的境况下,索隐派一直不被看好,成为了红学中被打击嘲笑的主要对象。索隐派红学出现时间比较早,虽经考证派与小说批评派的屡屡打击,但研究者不乏其人,影响从未断绝,不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惊涛拍岸之势,在红学的研究领域掀起狂澜。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作者回忆家族往事,带有深深忏悔的意味,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是一种鲜见的笔法,由不得让人去寻根究底。其实,胡适和周汝昌所认为的曹雪芹自传说,将这一“贵族家事”锁定为曹家,也未尝不是索隐了其中的一个家族。
但是考证派考证的愈深,却愈陷入一个重大的逻辑陷阱:如果按考证出曹雪芹出身于雍正二年的年龄,雍正六年曹家就被抄家罹祸,那时他仅四五岁,曹雪芹并没有经过曹家的全盛时期,如何写出如此一部绝大富丽典制文字?而且即便考证到了曹雪芹的完整的家谱及生平,仍然无法解释《红楼梦》中存在大量的碍语和密语。更何况随时间的推移,存世的证据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没得可考。
而索隐派却是以解密的姿态来研究,以史料的对照来做应证。解密法经过脱密的变换,将会得出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索隐派红学的研究特点是:研究家们层出不穷,风起云涌,不断将《红楼梦》中的各类人物,映射为自己解读的历史人物,都认为自己的解密将是唯一的标准答案,各执一辞,水火不容。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信息的查询与获取变得快捷高效,使得索隐派研究的最大困难:巨大的信息检索工作量,变成轻敲键盘触手可得,在信息技术大潮的推动下,一些国外的古老命题得到了重新审视,因此红学索隐派研究在海内外得到复活,渐成风起云涌之势。用信息手段重新审视我国重大谜题《红楼梦》,是历史趋势所然,也是如今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中的一支。
不管您对索隐派红学了解多少,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红楼梦》中存在大量的碍语和密语。《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镜中花、水中月,这表面的幻相是真相的光影折射。因此《红楼梦》并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用汉字密码写就的旷世奇书。我们先不要为“《红楼梦》弦外之音到底隐喻什么”而产生争执,而应该先把《红楼梦》既有表,又有里,具有双面性、二维性的事实肯定下来。而且正因为《红楼梦》兼有“表、里”的二维性,使得《红楼梦》卓然超越于众小说之上,让读者读之如观镜花水月,捉摸不透,欲罢不能;让学者忍不住要对其真相和幻相进行探究,从而形成一科专门的学问:红学。其实所谓红学研究“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学术纷争,正是体现在对“表”与“里”的不同认识上,考证学派研究的是“表”中所喻(明文、显学、作者家世、自传说),索隐学派研究的是“里”中所喻(密文、隐学、隐喻、弘外音)。双方各研究其中的一个维度,其发生的争执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因此谁也不曾说服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