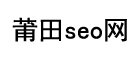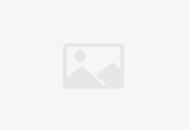五台山菩萨顶的前院东侧至今还立着清高宗1786年3月所书《至灵好峰文殊寺即事成句》碑,开首即说:“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是日章嘉国师率众喇嘛诵经迎驾)。”这里所说的章嘉国师,就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佑宁寺的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
生平右侧铜像头戴大折沿班智达帽,宽额丰颐,右面颊下长有一个小包,是其面相特征。身侧两枝莲花上分别置经箧与宝剑,与宗喀巴标识同,显示其崇高地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初十日出生在甘肃武威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个牧民家中,其父古茹丹增,原是青海湟水流域祁土司的属民,土族人,后举家迁往凉州放牧,落籍于当地的藏族部落。据说若必多吉自幼聪颖异常,恰值估宁寺向西北方向寻找二世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于康熙五十八年经理藩院奏准,认定他为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并于次年六月迎入佑宁寺坐床。章嘉活佛转世系统是清代甘青地区著名的大活佛,因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洛桑却丹曾被清圣祖封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主持内蒙古地区喇嘛事务,所以若必多吉从坐床起即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
清世宗即位后,青海蒙古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乱事波及青海藏、蒙古各部,佑宁寺的一些僧人也策划响应。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年羹尧、岳钟琪率领清军攻打佑宁寺,杀僧俗6000余人,毁坏全部寺院建筑。若必多吉在战争发生前被僧人带往大通河上游的森林中躲藏。清世宗因即位前曾向二世章嘉活佛学法,所以急诏年羹尧保护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年羹尧遂威迫佑宁寺僧人接回若必多吉。不久若必多吉在西宁出痘,清军为他延请名医治疗,康复后还设宴唱戏祝贺。当年清军又奉清世宗之命将年仅8岁的若必多吉护送到北京。
清世宗对年幼的若必多吉进京后的生活作了周到的安排,命他跟从当时在北京的佑宁寺二世上观却吉嘉措学习藏文和藏传佛教,同时还让他与皇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即后来的清高宗乾隆)等皇子同窗读书多年。因此若必多吉不仅精通藏文,还学会了汉、蒙古、满等民族的语文,在佛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清世宗到北京旃檀觉卧寺时,若必多吉出院门跪迎,世宗亲自将他抱起,进入屋中坐在同一坐垫之上。清世宗还准许若必多吉按前世所受封赏乘坐黄幛马车、坐九龙褥,以致当若必多吉的马车出入皇宫东华门时“都人士女,争取手帕铺途,以轮毂压过,即为有福。”1727年,清世宗发库银10万两在多伦诺尔建善因寺,赐给若必多吉居住,清世宗还为善因寺撰写了碑文。1734年,清世宗又照清圣祖册封前世章嘉活佛之例正式封若必多吉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册金印等。
1735年10月,当者必多吉在日喀则从五世班禅受戒时,传来了清世宗去世的消息,若必多吉匆忙从西藏返回北京,朝见新继位的清高宗,高宗立即下令将掌管京城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若必多吉,封他为掌印喇嘛,从此若必多吉成为最受清高宗宠信的驻京喇嘛。
若必多吉参与了清高宗在北京、热河等地兴建皇室喇嘛寺院的一系列工程。1744年高宗与若必多吉商议后改建清世宗即位前居住的雍亲王府为喇嘛寺院,这便是著名的北京雍和宫。雍和宫的所有宗教事务和僧人管理都由若必多吉负责。1751年清高宗为了祝厘其母六十大寿,改北京西郊瓮山为万寿山,若必多吉负责山后香岩宗印之阁的四层金顶佛殿的修建及殿内密宗佛像的塑造,并征集内蒙古各旗的僧人来此诵经学法。
由于若必多吉精通佛学知识和多种民族语文,因此他在乾隆时期翻译佛经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翻译佛经,若必多吉培养了一批藏、汉、满、蒙古等族的翻译人才,对清代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若必多吉既是在蒙古、藏区有很高声望的大活佛,又与清高宗有密切关系,因此他在清廷处理蒙藏事务时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1750年10月,西藏发生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乱。他提醒清高宗注意西藏的民族和宗教的特点,不要抛开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上层处理西藏事务,不要在西藏采用与统治内地相同的办法。在若必多吉的劝阻下,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清高宗决定将西藏的政教权力交给七世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务,由此确定了一直延续到近代的达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度。除了提出重要建议外,若必多吉还多次肩负特殊使命到西藏、青海等地,处理重大事务。1749年和1764年章嘉·若必多吉两次返回青海为母亲和父亲奔丧,每次都受到青海僧俗大众的热烈欢迎。1749年若必多吉回青海时向佑宁寺、塔尔寺、广惠寺、夏琼寺颁发了清高宗赐给各寺院的匾额(赐给塔尔寺的“梵教法幢”匾至今尚存于塔尔寺大金瓦殿)。并为拉卜楞寺二世嘉木样活佛、广惠寺三世敏珠尔活佛剃度授戒。1764年若必多吉回青海时还应佑宁寺僧众的请求就任佑宁寺法台,为僧众讲经说法,从青海各地前来听法的僧人达数千人之多。这些活动增强了青海藏、蒙古、土族僧俗与清朝政府的联系。
章嘉·若必多吉还利用他在蒙古各部中的巨大影响来帮助清高宗巩固对蒙古族地区的统治,解决一些突然遇到的难题。由于清高宗倚重若必多吉协助处理蒙古事务,所以若必多吉的影响所及不仅内外蒙古及新疆、青海,就是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的首领渥巴锡等人也对若必多吉十分崇信。
在日常生活中,清高宗数十年如一日地对若必多吉优礼有加,每逢年节、传法、诞辰之日,都要赐给着必多吉大量财物。1781年夏,清高宗与若必多吉一起上五台山,在菩萨顶举行析愿法会时,特意让若必多吉与他同坐在一个座垫上,并说:“与呼图克图坐在一个座垫上,朕便觉得安乐。” 1782年因黄河多年泛滥,河南龙冈缺口难以合龙,河堤工程紧急,清高宗又问计于若必多吉,若必多吉说应派员到青梅祭祀阿尼玛卿山神,对治河工程有益。于是高宗命乾清门侍卫阿弥达驰往西宁,会同西宁办事大臣留保柱、若必多吉之弟却藏活佛前往河源致祭,由此引出清代对黄河河源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察。1786年3月,清高宗去五台山,并命着必多吉三月赶至五台山接驾,君臣一起在五台山文殊菩萨像前举行祈愿法会。清高宗下山回京后,若必多吉染病不起,于四月初二在五台山去世,清高宗闻讯大为悲励,下令用7000两黄金造大塔一座,安置若必多吉遗体,在五台山掘石扈安藏,并命者必多吉的侄子拉科呼图克图去西藏为若必多吉做超荐法事。
身后若必多吉门徒众多,其中不乏当时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嘉木样·晋美旺波、敏珠尔·阿旺赤列嘉措等。若必多吉本人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学者,他一生著述甚丰,由弟子们收集刻版的全集共计七函,其中的《七世达赖喇嘛洛桑格桑嘉措传》、《藏文三十颂与字性添接法略解》、《宗派建立论》、《藏文正字学》、《北京白塔寺志》、《清凉山(五台山)胜地志》等,都是流传甚广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