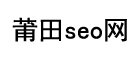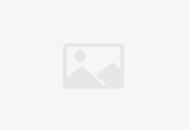苍岭古道
唐朝诗人孟浩然去天台经过缙云时就翻越了苍岭古道,刘昭禹也诗云:“尽日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步起,危径及天盘。瀑顶桥形小,溪边店影寒。”宋朝杜师旦诗云:“人云蜀道苦难行,我到云间两脚轻。”在文人墨客的咏叹中,苍岭的险峻比蜀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古道的开凿也当在唐宋以前。准确地讲,这条千年古道,是仙居走往内地的盐道。从晚唐年间开始,在仙居境内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河商业中心,从海盐县等地熬制的食盐,经浙江的第二大河流椒江,逆水而上,再经永安溪到达仙居的皤滩镇,慢慢地,皤滩逐渐形成了盐埠,并集结了运往内地的其他商品。而商业重镇的皤滩要往内地辐射,便要翻过高高的苍岭群山。苍岭古道,路宽足有一米,两人相向而行,不需侧身相让。路面用大块岩石铺垫,岩石光滑如镜,粗糙的路石竟被人们千踩万踏得如此光滑,这足令我们感慨万千。其实苍岭古道最险峻处在风门,正好位于缙云和仙居交界处的南田村。只见大山紧紧夹峙,只容古道蜿蜒而下,这是道天然的屏障,也是古道的制高点。据清《缙云县志》载:明嘉靖三十五年六月,浙江巡抚阮鄂当时在南田村口水龟山屯兵祭旗点将后,兵将神勇百倍下苍岭痛歼倭寇。可惜历数百年岁月后,当年高耸的点将台及台上的将台殿,都颓圮消失了。2004年,南田村自发集资修建了点将台和将台殿。出了风门口,才真正一睹古道的风采:芳草萋萋,杜鹃簇簇,山岚时聚时散,飞瀑掩掩隐隐。大山峰峦迭嶂,山势雄拔陡绝,古道蜿蜒曲折。
由于壶镇至南田公路的修建,苍岭古道变得断断续续,这次古道的调查,使我们明确了西苍岭古道(缙云段)如今仍保存良好的地段:从冷水村到岭中的苍岭古道,上半段较陡的以条石横铺,下半段稍平坦的则以条石直铺与溪岩筑成;从岭中到山口的路段,也以条石横铺为主;再一段是从老鹰岩茶亭到槐花树村,这三段古道与黄秧树村的短捧岭、黄秧树到羊上村的牛背垅、苍岭脚村的桥头梦岩三段合起来,西苍岭竟还有六段古道完整保存着,这应是缙云人的幸运和骄傲。1958年,仙居至缙云公路建成通车,苍岭坑村繁华热闹的历史便嘎然而止。该公路取道湫山,经杨岸,进入缙云县界后,通三溪,到壶镇,这样路径虽然远了不少,但避开了险峻的苍岭。
仙居十景“苍岭丹枫”为其一。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枫树,染浸着苍岭古道的万般景象,如果赶上夕阳晚照、枫叶红遍的时候,晚霞中如血染的苍岭,谁都会醉在其间。
可惜,这已是曾经的旧景,属于文人笔端留恋的一方之土,属于曾经盐夫的火红岁月,如今只保留在少数盐夫的遥远记忆里。挑盐的队伍已经散去,满山的枫树被砍伐一空,二者皆成历史,只有昔日那条盐夫艰难爬攀的古道,千百年来顽强地保持着厚实的基段,静静地蜿蜒盘绕在苍岭的深处。
当旅游的人们,一再把目光投向古时商业繁华之地——千年的皤滩,苍岭古道只能躲在它的后方,并为少众知传。那时候,当皤滩夜晚的灯火彻夜辉映着永安溪,当皤滩的商人在计算着一进一出的利润,当各色各样的消费在灯火辉映的河岸街道里沸腾地进行,我们的盐夫正奋力攀爬在偏僻的山路上。苍岭古道与盐夫,二者不可或缺,古道因盐而生,也因盐而日渐荒芜,在曾经同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合并成了一个历史人文的完整篇节。
于是,寻访盐夫与前往古道,也成了一并安排,不过,独走荒芜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古道,仍然要比寻访当年的盐夫容易多了。
古道历史这条千年古道,准确地讲,是仙居走往内地的盐道,从晚唐年间开始,在仙居境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河商业中心,从海盐县等地熬制的食盐,经浙江的第二大河流椒江,逆水而上,再经永安溪到达仙居的皤滩镇,慢慢地,皤滩逐渐形成的盐埠,并集结运往内地的其他商品。至今有文字记载的,有水埠头官埠、永康埠、缙云埠、金华埠、丽水埠、东阳埠、龙泉埠、安徽埠、河南盐栈等,五湖四海的商人竟然在偏僻的山区,开辟出一个如此繁荣的市场。而商业重镇的皤滩要往内地辐射,便要翻过高高的苍岭群山,这是最难于通畅的路段,位于仙居城西百里,与缙云县接壤,即台州通往金华、衢州的交通要道,史称“婺(金华)括(台州)孔道,一千年来挑盐的盛况象盐夫一样,络绎不断地绘制出一幅历史的画卷。
高高的峻岭,齐膝的深草,蜿蜒的石径,深褐的块石,苍岭的盐道上,一具具竭尽全力的肉身,组装成搬运的传送带,这条唯一往内地的艰难通道,用肉身笨重地辟开,于是,一条食盐运输干线,也造就了皤滩古镇商贾云集的一派繁荣。古往今来的商业半径,从没有越不过的地缘屏障。
望着层峦叠嶂的苍岭,走在弯曲的古道上,我一直把活着的盐夫看成疲倦不堪的群体,在某处默默地度着疲倦而古稀的晚年,当他们卸下沉重的担子,不会让一个外人轻易去接触那段山道上的历史。解放前,浙赣铁路贯通后,盐夫的队伍开始慢慢递减,直到文革期间,盐夫的需要不复存在,曾经用最大限度的负荷、长距离承担商品经济中最原始的搬运环节,在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挥汗如雨的疲劳身体已经过多透支了能量与盐分,由此产生的印象,他们应该是满脸的皱纹、僵重的肢体、硬朗而热腾腾的身体只能依稀可见。
所以,在空荡的山道上,以及后来的寻访工作,盛夏的炙热酷暑,确是费尽周折而又深感不安,而且,这期中,我一遍又一遍地设想那热背朝天、满含悲壮的沉重之旅,猜想盐夫的描述是多么地热烈、多么地强劲,脑际中勾画出健硕的脊梁和浑厚的山梁,于是我这篇文章也会多么多么的生动有感染力、多么迫不及待的高亢和让人神往。
至于盐夫的行程,还会不会一种新构出传奇般的故事,在前后几百年的时空里升起,我不置可否,我只期待这一次的行走,最后的结果能在归来之后,对他们有着崇敬与怜爱。
当地有段民谣:头戴凉帽哎,冷饭缠腰!一里三歇哎,不怕苍岭天高!当盐夫往复在高峻的苍岭山道上,压在我们心里的沉甸,有如那高高的崇山峻岭,历史没有给气概冲天的盐夫以丰满的特写——为商业流通提供一个环节的盐夫,搬运从来不是主角。
也许,对历史探访者来说,探访的对象,倘若年龄越大,便有越接近历史的感觉。我探寻到的挑盐夫,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叫郑福火老人,他和子女已经落户在横溪镇上,这个镇介于皤滩与苍岭之间。我没有身体力行地负重走过路,作为一个顶多背包族,去接近一个大半生都负重前行的老人,我把尊重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尊重老人,一定程度也等于尊重老人的生活,再说高一点就是尊重历史。
当时为了挑盐方便,老人竟然把家落在苍岭山下、盐夫必经的一个村庄——苍岭村,老人的整个家庭便于苍岭盐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老人初作盐夫的年龄为十六岁,很难想象,刚成年的齿龄,血气还未上涌,筋骨还未强劲,稚嫩的肩膀还没有经过预热,一开始就要从120或140斤试试身板。这个重量是入围条件,如果不能在这基础上加码,那从事这项工作的报酬就缺少意义,而且最短的挑担距离是走三天,翻过牲畜不能驮运的山路、越过马车牛车不能走过的荒山野岭、翻过盐夫必经的盘山路。于是,对重量的恐惧和耐力的担忧,又是稚嫩的小伙子要过的心理大关。
从事这项非常艰苦非常普及的工作,都是乡下人家里的精壮劳力。在讲究几世同堂的中国古代农村,这项工作毕竟不是应征出战、不是背井离乡、不是抗涝救灾、更不是净身进宫,尽管做母亲或妻子的隐隐心疼,要知道,家人的叨念、过分的留恋与心痛,是一种重压和否定,就成了扯后腿,这对于超强体力劳动者意味着什么。所以,皤滩附近的广大贫苦百姓,在无法参与皤滩的街市经营、无法把孩子送到学堂私塾里去,总之,差不多的同龄人,到了该为家里出力的时候,选择居然一开始就有局限性,于是,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年轻身体里有了本能的承重力,便去尾随一种理所当然的生活走向。参照远村近邻的小伙子、或者上辈,讨论来讨论去,只好把即将成年的儿子受雇于盐商,挑选一根趁手的扁担,加入盐夫队伍,犹如早早等儿子长大,象事先取好的名字一样,孩子一出来便男女对应。这样也好,少却了悲伤的场面、或没完没了的家庭内说服,父子、兄弟一同上路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还多了照应。
说到底,这也是一项正当职业,在小伙子谈婚论嫁之时,并不会受到姑娘的丁点歧视。能从事挑盐夫作,在提亲的时候,有一连串的统一说辞,身体健康、吃苦耐劳、不游手好闲、不成天向那一亩三分薄田讨饭吃,旧时的庄稼人,图的就是劳动力的保障,一个为家出力出汗的健全汉子。
于是,天还没亮,年轻的小伙子揉揉天亮前才合上的睡眼,母亲打好行囊,带上饭团和备用草鞋这些简单盘缠,耳后几句简单的叮嘱,无须契约、无须担保,带上盖有重量的凭证,便一头扎进破晓前的初白中。
一人一担的生涯匆匆开始了,得到的照顾通常是走在照应人的前面,姿势不对,步伐不妥,呼吸不匀,甩手过大,东张西望,都在纠正范围,新老结合的盐夫队伍努力调教着每个新的成员。还有,就是充饥时间,长辈塞过一个饭团,让他多吃一点。
前面传过来的话说到,“不着急,只要过得了苍岭,就没事”。能不能从事挑盐的工作,便只等苍岭来认证。
在上苍岭之前,要经过两个村庄,分别为苍岭坑和坎下村。如果一个外来旅行者,定会惊讶,很难想象在一个深山的村弄里,居然会有商业小街,百十步长,用溪石铺嵌而成,街两旁一间间高透的排门店面,可拆卸的木窗、摆放货物的石台,依稀保留着当年开店的基本构造,古道穿梭着商业的人气。
这项艰苦与简单的体力劳动,造就了商业环节中一个最平等、最齐整的队伍,个体差别统统消除,特权从来没有产生过,既定的组成序列从来没有被混淆,没有领队、没有监工、没有专职喊号、更没有组织和帮派,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身份,所有的约束都是多余——在整齐划一的走向上,肩上差不多重量,操着相同的口音,献出各自的力气,并一同赶路一起挑盐。
所以,盐夫白日一般不作停歇,天晴不分时日,但下雨就无法成行,因为雨水会打湿食盐,所以,这种日晒雨不淋的工作,也没有人中途摔担子。如果实在没办法,分给还有能力加重的别人,如若没按时到达,要处罚甚至赔偿,工钱也只好别人挣去。不是大灾大病,都不会拖累同行的盐夫,自动退出或留下来与下一队同路。
但途中歇息到底经常,尤其是在苍岭山道,据说是一里三歇。都知道,挑着重物登山,最怕彻底放松,所以,每个盐夫带着一根支撑杆,在歇息的时候,都尽量站立着支撑担子。支撑杆的底部是生铁块,走路时放在挑盐的另一个肩上,在担子的后端分担着货物的重量;在歇息时从肩头自然落地,发出响亮的金属声音。听到这一声如此塌实稳定,此时的盐夫便站立着,直接把担子放到支撑杆顶端,担子用一根绳子牵扯着,只需把担子拊住不倒即可。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发明,盐夫挑运的工具,本来很精简,没有多大改进空间中,这一个带着声响的支杆,也许是千百年来改进的一小步,已经相当了不起。
半山的一个石屋,几个老人焚香点蜡、鞠捧薄酒一杯,他们在缅怀先人走过的路。
秦始皇筑建万里长城,也是在崇山峻岭中,依靠男子的身体,将巨石层垒筑构起来,在他们头顶上,高悬着长戟与皮鞭,以国家的名义从事无偿的劳作;而盐夫是一种取其自愿的商业活动,不是硬性的终身选择,他们一样转运着不属于他们的物质,心中却惦记早已核定的不管等值抑或低廉的价格。
商队的脚印踏过丛林浓密的古道,没有停留、没有垒下任何东西,只有在白花花的太阳下,流淌的汗水,浸渍在山石与土方里。深褐色的大块石板,象一格一格的电影记录胶片,冲印出年代久远的故事。
商业社会的道路,历来非常现实,力气被开出的价格,完全是明码标价,一百斤一元的力钱,获得力钱的标准是食盐和人同时到达。
当然,在登山时,喘息间偶尔也喊出来,内容不成词、不成句、不成歌。山道上的枯燥,共享同路的孤独,晃晃悠悠的行走,山风穿过密密的林木,飞鸟越过上空和山涧,但绝不象他们挑的食盐那样有滋有味,山道上唯一提供的,是清冽甘甜的泉水,走上一段就接上几口。
就是这群挺直腰板、埋头走路的盐夫,在冬去春来、严寒酷暑中,在几十年如一日的两点之间,走出了一条输血一样的商业干线,走出了财富流通的南来北往,走出了皤滩日渐昌盛的新景象。
用双肩与双脚共创一段商业历史,于是这段历史也喘着粗气。
望着长天碧草的山岭,看不见草林掩藏下的古道,高高的苍岭脚下,每个盐夫都做过一次深呼吸。
夕阳西下,没有谁欣赏自己拉长的背影;山涧的溪泉,没有谁屏息是为了聆听;对面走来的盐夫,省略了最简单的相视而笑,埋头赶路中,所有消耗体力的其他行为都是浪费,包括说笑和打闹、唱几句山歌,甚至随心所欲的可能举动,所有月白风清的悠闲都是奢侈,即使心底有万端感慨。
几十年几乎完全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所见所闻、同样的话题和际遇、同样的装束与配置,盐夫们走在同一条道上,思想逐渐趋同,外在形象也高度趋于统一,盐夫们把最青春年华放到了这条古道。
但窒闷的苍岭山道,还是走来了怀古吊今、吟诗作赋的诗人才子,与一队队的盐夫擦身而过。
唐朝大诗人刘禹锡,这位写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句,当他望着高高的苍岭,那时候,苍岭还远非如今看到的样子,没有任何铺陈和修葺的道路,稀稀拉拉的往来盐夫引不起他的注意,住在小店中的他,异常落寞,起性写下了:“尽日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步起,危径及天盘。瀑顶桥形小,溪边店影寒。”
宋朝杜师旦诗云:“人云蜀道苦难行,我到云间两脚轻。”没有负重踏行的诗人、没有真实到过蜀道的才子,走到了苍岭上,刹时云里雾里。忙不叠地相让的盐夫,在他们的眼里,这些穿着宽大衣袖的人,走在山道上居然不用挑盐,心情实该闲悠,文学才能给读书人的优越感,盐夫仰望过去,是一座比苍岭还高不可攀的山峰。
再后来,元朝兵部尚书赵大佑,一身戎装,率领一队兵马,雄赳赳地走来,山道上有了衣甲鲜明、列队浩荡的场面。那时候,江南中原,已经征服在蒙古的铁骑下,天下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诗人的精神田舍里又开始着文人的骚动,所以,文武双全的尚书诗人,审阅苍岭的上上下下后,士大夫的文化素养油然而生,他便望岭题诗:“披襟入深雾,四山乱鸣泉。人疑来异界,身似向重天。犬吠云中舍,农烧涧底田。”六连诗句,前后沾捻,刀枪入库的递进,便一览无余。
还有仓皇南下的南宋时期,著名词人李清照,孤单独影地走过苍岭,身心疲惫、国破家散的她,可惜没有留下任何词句,词人没有让苍岭一道凄然。
这些游走在中华山水间、走过路过苍岭山道的文人们,怀揣“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辽阔志向,象一只凌空飞翔的小鸟,飞过苍岭古道,用鸟瞰的视觉,捕捉文化创作的上层元素,过滤一切与文学美相抵触的不和谐因子,也顺手过滤了盐夫的苦难与悲吟,然后营造了专供他们鉴赏的浪漫诗章。领管精神文化的才子们,活在远离流通领域的诗歌世界里,当然没有析出一丝盐夫的苦涩或者咏叹,在他们眼里,苍翠的盐道山路也与盐夫无关。
后世的我们看来,山道毕竟有了盐夫以外的人们,山道的色彩因此也闪烁着一些亮色,不再只是纯粹的苦难。晚清末年以后的百年,人工种植的满山枫树,染透了苍岭和天色,古道披挂着绚丽一时的风景,红灿灿燃烧着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苍岭山道达到了商业的最高沸点。
如今,古道没有彻底荒芜,但已不再只是盐夫的专用道路。解放之前,浙赣铁路逐段修筑贯通,这条东部沿杭州、金华通向内地的大动脉,盐业及其他货物搭上了现代化运输,从不相互抢道的盐夫,终被现代化抢道了,苍岭盐道的高投入低收益、以及运送时间都无法与时代对应着换算。
不过,郑福火老人,以及他的同伴,直到文革期间还在吃力地挑盐,苍岭山道的历史功能总舍不得一下子收尾,直到没有精力挑下去,有如温州的某地,如今还在保留最原始的宋代工艺,生产粗糙的竹质纸张。
修建高速公路的临时道路,在古道的对面山上,平缓且反复盘绕,最后也到达古道的同一个顶端——缙云南田村,但这条路,除了修路工人用,南田村的人到山下的横溪镇,还是要上下古道。看看古道上三三两两的青年游客,看样子,被称为“古道”后,又有了新的历史任务。当我奋力走到古道顶端,看到南田村,我惊讶了好久,以为古道是进出这个山顶村庄的唯一通道,然后又听说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村,居然每天还有三个班次的中巴车,接送着过山的人们,到另一端的缙云县的壶镇和县城。霎时,我感觉今天好象做了与盐夫相同的事情,把自己艰难地送到此处,然后把自己交给另外一种转移方式。
南田村的山岗旁,新砌了一个方正轩昂的“点将台”,是纪念明朝年间浙江巡抚阮元总督漕运时,在此所留的事迹。作为明朝封疆大吏,也是明朝大科学家、大书法家,他率先在学术界提出了计算容积的简洁方法,建立了测量容积的石、斗、升、合的度量系统。而这样一个十六世纪先进的系统,与世界同步的配套理论,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却被闭关锁国的国家闲置起来,他离开的四百年后,就是这条盐道上,人们还在肩挑背扛,一千年如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
等待全线贯通的台金高速,即将完整穿越苍岭隧道,田野间一座座高架已经形成,再以后,古道将进一步失效,接天碧绿的遮盖中,等待怀古的人们前来走上一遭。
“沧岭丹枫”本为仙居一景,如今到苍岭下的车行便道已经接通,寻不到一棵枫树的苍岭古道,让几个投资人犹豫不定——到底要不要开发出一个旅游景点。